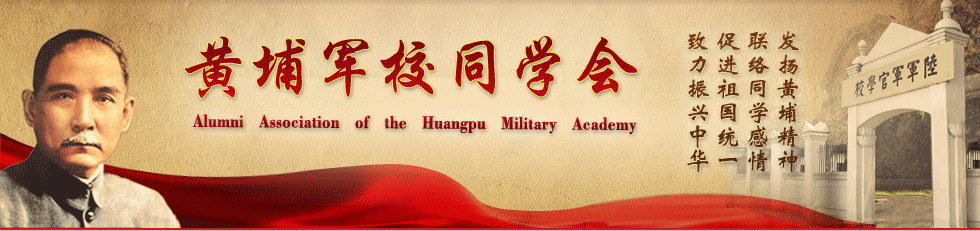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時期,從甘肅省東南部重鎮、古城隴西縣的我家門里,走出了三位黃埔軍人。這莫說在當時經濟衰敗、城市蕭條的隴西縣絕無第二家,就是在廣闊的西北大后方亦屬罕見。這其中的原因還得從我的祖父說起。
我的祖父張和平是位愛國憂民的讀書人,曾任過隴西縣郵政局局長、縣政府參議員,還憑著早年在蘭州市黃河北麓由外國傳教士興辦的仁愛醫院(現蘭州市第二人民醫院)里當司藥時學到的西藥知識,在隴西縣比較熱鬧的萬壽街丁字路口開辦了一所“和平大藥房”,在隴西城里也算得上是位有頭有面的人物。他為人豪爽,樂善好施,開明正直,嫉惡如仇,對子女教育嚴格,秉承“幼兒養性、童蒙養正、少年養志、成年養德”的傳統教育模式,從小給他們灌輸“盡忠報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法古今完人”、“明理義、知廉恥”、“端正屹立”的愛國思想和做人準則。所以,當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面對國難當頭、民族危亡的緊急時刻,他深明大義,鼓勵支持血氣方剛的愛子們一個個進軍校,學本領,上戰場,保國家,投身浴血奮爭的戰斗行列。
如今,我的先輩們都已離開人世,但他們胸懷滿腔愛國激情,用血、汗、淚書寫的黃埔軍人的壯麗人生故事,卻深深地鐫刻在我的心中。
伯父張世英
我的伯父張世英(1914—1937),字俊山,出生于1914年,是家里的長子,祖父對他寄予厚望,從小嚴格教育,期待他長大后成就一番事業。伯父自幼謙和親孝,品學兼優。1928年就讀甘肅省立隴西第五師范時,在隴西縣各界歡迎抗日名將吉鴻昌將軍的大會上,被推舉為學生代表致歡迎辭,一時鄉里交口稱譽。1930年,隴西第五師范校長王福隆向縣政府追索積欠經費時,被時任縣長邊仙舟唆人打傷,全校師生群情激憤,游行抗議。當隊伍行進到縣府時,縣長竟調集警察鳴槍彈壓,伯父挺身而出,一聲怒吼:“有膽量的朝我開槍!”游行隊伍一擁而上,嚇得警察狼狽后撤,縣長翻墻而逃,后被革職。
伯父酷愛書法,寫得一手好字,曾被當時隴西的著名書法家楊芷嘉先生譽為“翰墨天才”。1931年師范畢業后,伯父考入甘肅學院(蘭州大學前身)教育系。正當他勤奮讀書,立志將來要當一位誨人不倦的教師時,爆發了九一八事變,東北疆土相繼淪陷。伯父義憤填膺,在祖父贊許下,決然于1933年去南京考入黃埔軍校10期2總隊步科,期間與志同道合的同班同學張學思(張學良將軍胞弟,中共黨員,解放后曾任遼寧省人民政府主席、海軍司令部參謀長)義結金蘭,情同手足。1936年冬軍校畢業,伯父回家省親,對弟弟們講了許多在黃埔軍校的習武生活和時局形勢,并教誨大家要愛國家、愛民族、做中華好男兒,隨時準備以身殉國。
1937年春,伯父南下廣東韶關,到15集團軍11師羅卓英部報道。孰知這一去竟成永別。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軍民全面抗戰開始。日本強盜妄圖憑借陸海空軍優勢及先進的軍事裝備,“速戰速決,三個月亡華”,在向我華北進犯的同時,8月13日又猛攻上海,拉開淞滬會戰序幕。國民政府緊急調動幾乎占當時全國三分之一的兵力,“火速開赴上海參戰”。伯父隨軍開往上海。出征前,伯父從韶關寫給我父親一封信,信中說:“我師奉命即赴上海作戰。男兒報國殺敵,血染疆場,馬革裹尸,夙愿將償。自古忠孝不能兩全,如我殉國,切記當繼吾志……”這竟成了伯父的“絕命書”!伯父從此杳無音訊。
1940年,我父親在87軍參謀處任職時,寫信給當時已劃歸該軍建制的11師師長葉佩高,請求查找其兄下落。后得該師部回公函方知,伯父所在的11師1937年8月下旬奔赴上海參加淞滬會戰,布防后人比作“血肉磨坊”的羅店鎮一線,與日寇反復血戰。伯父初任排長,在羅店爭奪戰中,連長陣亡,伯父陣前受命接任連長,率部與日寇殊死搏殺6晝夜,于1937年9月7日,不幸頭部中彈,英雄犧牲,成仁取義,全連戰士僅存7人。伯父殉國時,年僅23歲。據1990年版的《隴西縣志》載,抗日戰爭時期的隴西籍革命烈士共有49人,伯父張世英屬首位為國捐軀者,已追認為革命烈士,其英名和小傳亦載入史冊,永為后人景仰。
父親張世雄
我的父親張世雄(1917—2004),字漢三,1917年2月19日出生于蘭州,在兄弟間排行老二。1935年從甘肅省立蘭州中學高中畢業后,考入山東齊魯大學醫學院。1937年七七事變后,全面抗戰爆發,日軍大舉進攻,沿海許多城市相繼淪陷,父親和一批當時在外省讀書的甘肅籍學生,陸續返回甘肅。他到蘭州后,轉入甘肅學院繼續讀書,并立即投入抗日救亡活動,在八路軍駐蘭辦事處謝覺哉、孫作賓等負責同志的支持和領導下,組織起蘭州市第一個抗日救亡團體省外留學生抗戰團。父親還與同學聶青田、尚德延等人,聯合蘭州中等以上學校的同學和社會上一些熱血青年,組織成立了有50多人參加的“血花劇團”。大家齊心協力,克服各種困難,排練演出了多部宣傳抗日的劇目,在社會上反響極大,一時間,蘭州學生運動熱火朝天。后來,甘肅學院學生會發起組成甘肅省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公推我父親擔任主席,為甘肅的抗日救亡運動做出了貢獻。
1937年11月,歷時3個月的淞滬會戰結束,上海失陷。12月13日,日寇侵略軍攻占南京,在此后一個多月的時間里,血腥屠殺了30多萬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和中國士兵,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年屆21歲的父親怒火滿腔,再加上當時兄長音訊全無,感到已遇不測,他決心繼承長兄遺志,誓報國恨家仇。在祖父的支持下,他毅然淚別已有身孕的妻子,離開蘭州,南下四川銅梁,考入黃埔軍校16期2總隊步科,學習殺敵本領。
1939年夏軍校畢業,父親即被派往戰斗正酣的湖南長沙九戰區79軍98師駐守的最前線任排長,參加了和日寇在湖北通城縣進行的極其慘烈的拉鋸戰,部隊傷亡重大。此役后奉調87軍43師,從此隨該軍轉戰湖南、湖北、江西、貴州、廣西、四川6省,與日寇鏖戰6年,歷經長沙、湘西、鄂西、桂柳四大會戰,九死一生,屢立戰功。
1944年,日寇進犯廣西,侵占桂林,又向貴州南部進犯,43師奉命星夜趕赴黔南增援。那時,父親已調升43師第127團1營營長,率部與友軍一起將日寇攆回廣西柳州,部隊遂駐防黔南。
1945年初夏,父親隨軍開赴湖南接近廣西的龍勝地區待命。7月初,94軍奉命由龍勝地區從北向南,與友軍71軍鉗形夾擊桂林日軍,限月底奪取此戰略要地。127團的任務是攻占桂林北面屏障龍勝地區的丁嶺界。部隊秘密行軍,于7月13日接近了丁嶺界。這是一個五角星形的山頭連鎖陣地,由日寇一個山地戰特種兵聯隊防守,敵人經過一年的經營,防御設施和火力配備非常嚴密,大有“一夫當關,萬夫難越”之勢。127團1、2營擔任主攻,時任1營營長的父親隨團長等花4天時間做了周密的地形偵察及動員準備,于7月17日拂曉發起猛攻,在美國空軍及師炮兵的支援下,反復與日寇展開拉鋸戰,至下午2時,全部占領丁嶺界,接著又一舉攻占了金辦坳日寇據點。此役雙方都付出了重大代價。殘敵向南潰逃,父親又奉命率部作為先頭營尾追日寇,一路攻取了宛田大嶺天險,夜襲田鎮,截獲日軍大量物資和武器彈藥,一直追到桂林北六十里鋪。桂林日寇主力部隊棄城東撤全州。部隊急行軍,于7月27日上午占領桂林西關,殘敵已將桂林護城河橋炸毀逃遁。此時,友軍先頭營也到達西關,兩軍勝利會師,收復了桂林。這時的桂林城郊及飛機場全毀于戰爭,成了一片瓦礫焦土,部隊只好到城東10里以外的村落扎營整補,準備繼續奪全州,取衡陽。
8月15日晚,忽然從無線電里收聽到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消息,人們立時互相擁抱,喜極淚飛。中國軍民艱苦抗戰,終于贏得了最后的勝利。1945年9月7日,43師作為全軍先遣隊,乘美國運輸機直飛上海,收繳日軍武器,接管防務。這天正巧是伯父張世英殉國8周年忌日,父親一下飛機,百感交集,熱淚滂沱,爆發出悲壯的呼喊:“親愛的大哥,弟弟已完成了你的遺愿,為你報了仇!日本鬼子戰敗投降,上海已經收復,你可以瞑目安息了!”之后,父親又隨軍飛往北平、天津、唐山等地,收復國土。旋即奔赴東北,從蘇聯紅軍手中接管了沈陽市。
1945年12月,父親升任師部上校軍械主任,駐防唐山、天津一線。1947年,該師調赴東北,任43師司令部上校副官主任的父親,因不滿內戰,裝病(抗戰時腰部負過傷)拒絕去義縣北鎮興平打虎山一帶與人民解放軍作戰,并發表反戰言論,遭到逮捕,被押解往天津軍法審判,途中承黃埔校友幫助逃脫,經海路跑到上海。當時,國民黨天津警備司令部以“通共嫌疑罪”對他發出通緝令。父親不敢久留,長途輾轉,終于1947年底,回到甘肅省天水市。自父親1937年離家抗日,一去十年多,我出生在天水外婆家,并在外婆一家的關愛下度過了童年,和母親一起苦苦等待著父親勝利歸來。現在他總算活著回來了。我那時已經10歲,讀小學四年級,才頭一次見到父親的模樣。當時,中國有多少熱血青年,為救國家離鄉背井,舍妻別子,奔赴戰場,“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譜寫了可歌可泣的中華民族壯麗樂章。1948年春節過后,母親和我隨父親回到了隴西老家。
1948年,父親受國民黨甘肅省保安司令部的委派,任隴西縣民眾自衛總隊副總隊長。1949年6月,又被甘肅保安副司令兼師管區司令的周祥初將軍委任為該部隊補充一團上校代團長。當時,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強大攻勢下,國民黨政府垂死掙扎,西北軍政長官馬步芳妄圖挽救殘局,抓兵搶糧,橫征暴斂,民怨沸騰。早已對國民黨失去信心的父親,經老軍長周祥初將軍(解放后曾任甘肅省軍區副司令員、政協甘肅省委員會副主席)指點,通過黃埔軍校15期學長、當時公開身份為甘肅師管區騎兵補充團團長的地下中共黨員康君實與當年甘肅學院的老同學、時為共產黨地下武裝“隴右游擊支隊”副政委的萬良才(解放后曾任隴西縣第一任縣委書記兼縣長、中共甘肅省委秘書長、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取得聯系。萬良才化名楊仲義多次宿住我家,與父親密議,暗中聯系進步人士,控制地方武裝力量,伺機起義,迎接解放。他們的活動,很快便被國民黨特務嗅出了氣味。一天早晨,父親出門上班,發現大門上貼著一張紙,上面畫著一支手槍,下面寫著醒目的兩行字:“張世雄膽敢通共背叛黨國,小心吃槍子!”這引起了他的警覺,立即調兵站崗警戒,并加強城關巡邏,以防不測。8月初,解放軍進攻天水,國民黨120軍周嘉彬部、黃祖勛部及“馬家軍”的接兵部隊從隴西一線倉皇西撤。周嘉彬臨走前召見我父親,下令必須將隴西庫存糧食一律燒毀,不能“留以資敵”。8月7日,該軍后衛部隊撤離隴西城防。父親看到機會來了,一面緊急調兵控制城防,把守糧倉,維持治安;一面派出由祖父張和平牽頭的由8位開明紳士、社會賢達組成的談判代表團,與隴右游擊支隊聯系,談判商簽和平解放協議。8月8日,父親召集隴西軍、警、政、鐵路、教育等各方面的負責人到縣政府開會,宣布起義,走“和平解放”的路,大家一致熱烈擁護。8月9日,雙方代表簽訂了“隴西和平解放協定”,父親即去佛惠寺會見了共產黨隴右游擊支隊司令員毛得功、政委陳致中等,并迎接萬良才等人進城接管隴西政權,隴西縣遂告和平解放。8月中旬,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第1兵團司令員王震將軍率領大軍過隴西,直搗馬步芳的老巢西寧。父親全力完整保存下來的大量糧食,有力支援了解放大軍,王震將軍特地接見并表揚了他,并囑咐在場的縣黨政領導要好好對待這位“對人民有功的共產黨的朋友”。
解放后,父親為了孝敬年已花甲的父母,謝絕了萬良才等人讓他加入王震部隊的美意,脫去軍裝,結束了軍旅生涯。憑著當年曾在齊魯醫學院學到的一些知識,經營起祖父開辦的大藥店,開始了醫務生涯,還當了隴西縣衛生工作者協會副主任。之后,父親因國民黨黃埔軍官的身份蒙冤多年,但他深信自己熱愛國家,抗日有功,起義無罪,總有一天黨和人民政府定會尊重歷史,做出公正評價,還他一身清白。憑著這樣的堅定信念,靠著黃埔軍人練就的好身板和剛毅豁達性格,父親挺過了那段艱難歲月,盼到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春回大地,改革開放。1981年,父親的問題被徹底平反,宣布無罪,落實政策,當上了政協隴西縣常委、政協定西專區參政議政員。
這時,已年逾花甲的父親猶如枯木逢春,生機再發,積極參政議政,撰寫文史資料,開辦診療所,為群眾服務。1989年,甘肅省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父親立即參加,并擔任了隴西縣黃埔聯絡組組長。1991年母親病逝后,我便將已屆75歲的老父親從隴西老家接到蘭州安度晚年,很快他便融入到甘肅黃埔軍校同學會蘭州市七里河區聯絡組這個戰斗集體內,還擔任了省黃埔軍校同學會聯絡委員會委員,踴躍參加同學會各項活動,以高度的愛國熱情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盡力。1996年,他被省同學會評為優秀會員。
2004年6月16日,已88歲高齡、身體日漸衰弱的父親,堅持參加了紀念黃埔軍校成立80周年慶典活動。回家后表示,還要爭取以血戰日寇的黃埔老兵身份,參加2005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活動。不料他未及等到這一天。2004年9月13日夜,父親悄然辭世,走完了一個愛國革命黃埔軍人的人生歷程。他留給我們最后的話是:“我這一生總算對得起國家、民族,知足了!”2006年10月,政協蘭州市七里河區委編輯出版的《七里河區文史資料》(第四輯)一書中,刊載了一篇區政協委員、黃埔聯絡組副組長肖熙澤等撰寫的文章《愛國黃埔軍人張世雄》,將我父親的生平事跡留駐史冊,為人緬懷。
四叔張世杰
我的四叔張世杰(1924—2005),字化民,1924年8月23日出生在隴西,在兄弟間排行老四。他從小極具音樂天賦,生就一副好嗓子,五六歲還未上學時,就能憑聽力把兄長們在學校里學到后回家哼唱的諸如“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等頌歌,準確無誤地唱出來,而且時常把街巷里和他年齡差不多的小伙伴們約集到我家門口教給他們唱,大人們見狀都嘖嘖稱奇。1931年,不滿7歲的四叔入隴西師范附屬小學讀書,備受音樂老師青睞特加培育,每逢“4月4日兒童節”和“10月10日國慶節”等全校紀念日活動,都要讓他登臺獨唱表演,成了縣上小有名氣的“童子歌手”。
1937年進入隴西中學讀初中時,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在音樂界一批愛國革命志士的奮力推動下,一場空前的大唱抗戰救亡歌曲的熱潮在全國掀起。當時已頗有些名氣的青年音樂家王駱賓一行人,為喚起民眾投入抗戰,奔赴大西北,一路傳播抗日救亡歌曲,途經隴西縣停留了些許時日。他們應邀到隴西中學教唱抗日歌曲時,王駱賓慧眼識珠,很快發現我四叔是個音樂天才,非常喜愛,經學校同意,四叔便成了王駱賓的弟子和幫手,跟著他們到機關、團體、學校及駐軍營地教唱抗戰歌曲。幾天下來,王駱賓給四叔贈送了不少還未及教唱的歌譜資料,并剴切指教音樂知識。王駱賓一行離開隴西后,四叔就成了校園里教唱抗戰歌曲的小音樂老師,有時還被別處請去教唱,成了“大紅人”。時隔56年后的1993年,早已譽滿全球的中國民族音樂家王駱賓應臺灣民族文化基金會邀請訪問祖國寶島,在出席臺北市實踐堂舉行的“王駱賓之夜”盛會上,與我四叔重逢,回憶往昔,激動不已,這兩位年齡相差十幾歲的“老朋友”,攜手登臺,縱情合唱了幾首大陸西北民歌,滿座贊嘆,掌聲雷動,立時成為海峽兩岸文化交流的一段感人佳話。
1942年,四叔高中畢業。當時抗日戰爭還在艱苦進行,18歲的他,立志沿著兄長們的路,到四川去投考黃埔軍校,獻身國家民族,同樣也得到了祖父的支持。恰好,當時正在遷至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新聞系讀書的三叔張世豪放暑假回家,四叔便跟著三哥到了重慶,正趕上同屬黃埔系列且設有音樂科的中央戰干團校招生,就報名考進了戰干團校。1944年以優異成績畢業,即被派往華東抗日戰場任軍樂指揮官。抗日戰爭勝利后,奉調浙江嘉興軍校任音樂教官。
1949年解放前夕,四叔隨軍校遷往臺灣,調派到由蔣經國當主任的國防部總政治部主管文宣的政二組任音樂宣傳委員會主任秘書。1951年春,蔣經國發起“軍中文藝運動”,成立了“軍中文藝運動工作委員會”,先后組建音樂界、電影戲劇界及美術界三個協會,四叔被委派負責音協方面的業務工作。后來,“軍中文藝運動”偃旗息鼓,“工作委員會”撤銷,四叔便乘機請辭離開軍界。1953年,四叔應聘到臺北市有名的建國高級中學任音樂教員,同時兼任司法官訓練所音樂講座教師,開始了他致力音樂教育30多年的人生新歷程。
1958年春,四叔懷著要在臺灣加強推行音樂藝術活動的愿望,和臺北女師音樂教師陽永光一道,開始組建一個純教育性的業余音樂藝術團體“中華合唱團”,經半年的艱辛努力,由“教育部長”張其昀批準,“中華合唱團”于當年10月5日在臺北正式成立。合唱團尊張其昀為創辦人,何應欽擔任名譽團長,四叔任團長,陽永光任指揮(后陽先生病逝,指揮一職便由四叔兼任)。合唱團的團員來自社會各階層,有教師、公務員以及在校的大專和高中學生,均為具有音樂基礎的優秀青年,雖流動性大,但經常能保持百人以上的陣容。建團之初,四叔便立下了一個三句話的“團訓”,叫做“貢獻最高的貢獻,享受最低的享受,犧牲最大的犧牲”。其實,這也正是他自己一生立身處世的準則。他以“士志于道”“擇善固執”的毅力和決心,面對各種艱難困擾,從不氣餒地帶領“中華合唱團”舉辦演唱會,參加島內外各種音樂交流活動,以及參與勞工、慈善、社會團體、學校、機關、醫院等的各類演唱活動,演出達數百場次,成績斐然,享譽臺島,聲揚海外,受到臺灣教育主管部門褒獎。“中華合唱團”自成立后30余年中,先后選拔訓練團員達15000余人,歷屆團員中獲得博士學位者不下百人,曾數次到北京演唱過的臺灣著名歌唱家范宇文就是其中之一。她在敘說其成長之路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我所有的音樂基礎知識,可以說全是張世杰老師教導出來的。因為我的用功,引起了他的注意,把我從一個合唱團默默無聞的團員,培養成為首席女高音,經常擔任獨唱的角色。他給予我的那種被肯定的信心及鼓勵是我一生感激不盡的。”
四叔在建國中學任教的數十年中,除了教授音樂課,還多年擔任高一、高二班級的級任導師,他以“亦師、亦父、亦友”極富人情味的獨特教學方式和剛直無畏、坦蕩真誠、重義輕財、不計毀譽的個性魅力,深受學生們的愛戴和敬重。建國中學地處市郊,平常放學時,校門旁的公共汽車站等車學生大排長龍,過路公車往往即使不全客滿到站也不停,四叔聽說后甚為不滿。有天放學后,他特到公共車站去看,果然見到一連有四班公車噴著黑煙飛馳而過,一點停的意思都沒有,足足等了半個小時,學生們怨聲載道。當又一班公車臨近時,四叔突然沖到馬路中央就地一躺,伸開四肢擺成個“大”字,嚇得原先沒準備停車的公車司機急忙剎車,待到車停門開,四叔也站了起來,一時愣住的學生們立即報之一片掌聲。“張老師俠骨義膽以身攔車幫學生”的故事立馬傳將開去。又有一次,四叔班上一位男生課間休息時,在教室門框上“吊單杠、蕩秋千”,恰被學生們背后稱為“雷公”的訓育組長撞見,抓去訓導處,激怒了四叔,他立刻趕去訓導處大聲理論:“學生尚年幼,偶犯小錯也屬正常,指出來讓他知錯改正就是了,憑什么非要小題大做,苛責嚴懲才罷休,這對學校又有何益呀!”學生雖帶回來了,但還是被記了兩個警告。第二天,四叔給這位學生記了兩個嘉獎,以示抗議。四叔退休后,有一年校慶,校友大聚會,他應邀參加,時任臺北市長馬英九和海基會前秘書長焦仁和也受邀蒞會。這兩位政要當年都曾是我四叔任導師時班上的高足門生。他們見到我四叔,連忙起身離座,走到他面前,先行個鞠躬禮,再恭敬地喊一聲“張老師好”,大家眼見這一感人場面,莫不動容。
四叔是一位性情中人,他熱愛祖國,心縈故鄉,眷戀親人,但殘酷的現實卻讓他孤身一人飄落臺灣,日夜渴望著返回故鄉。但海峽兩岸當時還處在敵對狀態,臺灣當局嚴禁臺胞赴大陸探親的政策讓他有家難歸,特別到那些“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日子,他總是把自己關在學校中破舊小樓內供單身教師居住的小屋里,把當年撤離大陸時悉心保存的父母兄弟姐妹的舊照片取出來,拿個放大鏡,流著淚,一張張反復細看,那種撕心裂肺的思念,常讓他失聲痛哭,徹夜難眠。直到1970年,他已40開外,在同事朋友的一再相勸撮合下,感覺回鄉無望的四叔才婚娶成家,后生一女一男。
1976年10月,鄧小平復出主政,平反冤假錯案,實行改革開放等訊息,通過新聞媒體接連不斷傳到臺灣,四叔心中已熄滅的回鄉火焰復被點燃,但臺灣當局的禁令尚未取消,大陸的親人音訊全無,生死不知,如何是好?正在無可奈何之時,四叔在臺灣的摯友,時任美國夏威夷大學終身教授的當代著名美籍華人學者、原籍甘肅隴西的羅錦堂先生電話告知我四叔,他準備去大陸并要到隴西探親。四叔喜出望外,拜托好友去了一定要幫自己打聽家人的消息。1980年,羅教授回到隴西,很快就找到了解放前在隴西中學的老同學、我的六叔張世舜,頭一次把四叔在臺灣的消息帶給了家人。羅教授返回美國后,立即將“家人全部平安,家鄉日新月異”的佳音,詳細轉告給我四叔,更堅定了他回家鄉、見親人的決心。
1987年4月,四叔利用代表臺灣基督教會聯會赴美國交流訪問的機會,從紐約打越洋電話到隴西一中,與已擔任政協隴西縣副主席的六叔取得聯系。回臺北后,四叔做了充分準備,9月中旬便以申請到美國夏威夷去探望好友羅錦堂教授為由,辦好簽證,只身離開臺北,秘密取道香港,在朋友的幫助下,經中國駐港新華分社的周密安排到了廣州,乘民航客機于9月22日直飛蘭州。
一下飛機,四叔即受到在機場等候的中共甘肅省委臺灣工作辦公室工作人員的熱情接待,隴西縣委得訊也即派統戰部部長和我六叔等于當日下午趕赴蘭州迎接。當晚,省臺辦為四叔舉行洗塵接待會。第二天,四叔回隴西途經定西市時,定西地委臺辦在賓館舉辦了接風會,廚師還特意做了一道叫做“燕歸來”的菜肴,送到四叔面前。下午,汽車還未駛進隴西縣城,四叔早已淚流滿面,從心底里發出呼喊:“親愛的故鄉啊!你離家42年的游子終于回來了!”到了縣招待所,一下車,便見到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二哥張世雄和幾位從未見過面的晚輩們,親兄弟見面,擁抱痛哭。當晚,兄弟三人同住一室,徹夜長談,傾訴42年的風雨經歷和思念之苦,當他得知父母、大姐、三哥 都已先后離世時,更是痛哭不已;當得知二哥張世雄已擔任縣政協常委、六弟張世舜擔任縣政協副主席后,稱贊說:“你們是共產黨的朋友,好!好!”次日上午,隴西縣舉行了頗為隆重的接待會,縣委、縣政府、人大、政協主要領導都出面,以富有家鄉風味的菜肴,宴請在臺灣的隴西籍人中第一位回鄉探親的張世杰先生及其在隴西的親屬。
此后兩天,四叔在兄弟陪同下,走親訪友,參觀、品嘗家鄉小吃,所到之處深切感受到家鄉的溫暖和鄉親們的深情厚意。他一遍又一遍地說:“真想不到,真沒想到家鄉變化這么大!真想不到,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并不像臺灣當局一直宣傳的那么可怕!”來大陸前心中的各種疑慮完全化解了。由于簽證日期有限,使他不能在隴西縣多做停留。9月25日,他懷著依依不舍的心情,在二哥張世雄的陪伴下,由隴西返回蘭州。縣委原準備派車直接送他們到蘭州,但四叔想乘坐火車看看沿途風光。縣委派車送到隴西火車站,統戰部人員同車站聯系,車站非常重視,車務段姬段長、車站王站長、調度室喬主任親自和177次列車聯系,幫助安排了軟臥包廂,列車乘務員得知四叔是闊別家鄉42年的去臺親人,十分熱情。列車即將啟動時,四叔熱淚盈眶,對送行的親友和縣統戰部工作人員說:“看到你們生活得這么好,我高興啊!我這是高興的眼淚啊!”
到蘭州后,又與在蘭州的五弟張世堯、二妹張世偉、三妹張世瑗及侄子、侄女5家20余口親屬歡聚數日。臨別前,省委統戰部、省臺辦有關領導又特為他舉行了送行招待座談會,四叔激動地說:“我遠離家鄉、流落臺灣42年,在那邊聽到的大都是反共反華的惡意宣傳,這次冒險回來探親,一路上受到的都是熱情接待,親眼見到的情景和臺灣當局說的完全不一樣,特別是家鄉的發展變化完全出乎我的想象,鄧小平先生領導的改革開放實在太偉大了。多次聽了各級領導給我詳細介紹共產黨對臺灣的政策主張,我舉雙手贊同。其實在臺灣,凡是經歷過抗日戰爭的人,尤其是愛國的黃埔軍人,都希望祖國強盛繁榮,永遠不再受人欺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無論如何是不會長久分裂下去的,一定會統一的,同胞親人一定會團聚的!”
四叔沿原路秘密返回臺灣后,精神振奮,立刻將“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而盡力”的決心付諸行動,積極協助國民黨元老、前“立委”、《中華雜志》創辦和發行人胡秋原老先生廣泛聯絡政、學界名流和有識之士,于11月22日在臺北舉辦了“中國民主統一問題座談會”,并在此基礎上,發起成立了“中國統一聯盟”,我四叔擔任顧問,與“臺獨”勢力展開斗爭。“中國統一聯盟”不斷壯大,成為一個在臺灣很有影響力的反“獨”促統社團。1989年,臺灣當局終于解除禁令,允許在臺老兵赴大陸探親觀光,四叔便名正言順地再次回鄉探親,帶回不少“統一聯盟”在臺活動的影像資料和出版物,交給省臺辦及贈送親友。1990年,他又隨“中國統一聯盟大陸參訪團”到北京。2月19日,受到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此后,每隔一二年,總要回來一次,每次與親人歡聚,都令他興奮不已。回到臺灣后,他廣為宣傳大陸觀感,并把帶回的紀念品分贈給親朋好友。他總想要為故鄉多做些貢獻,當得知“希望工程”的建設情況后,便在臺灣甘肅同鄉會發起成立了“甘肅旅臺人士資助家鄉艱苦小學聯合獎金管理委員會”,被推選為主任委員,他每次回來探親,都要把資助款和資助人員名單親手交到省臺辦,請他們代為選贈。
2002年10月他最后一次回鄉探親時,在省臺辦張溫璞主任、省黃埔軍校同學會王身璋會長、渭源縣委領導和二哥張世雄的陪同下,專程到渭源縣三河鎮回民學校捐贈款物,并代表臺灣甘肅同鄉會在該校師生舉行的歡迎儀式上發表了講話。十幾年中,他們累計向隴西、渭源等地的19所農村小學捐助人民幣數十萬元,他們造福桑梓的義舉,深受家鄉父老的贊揚。
2005年5月24日下午,四叔因心臟病不治,在臺北辭世,享年81歲。海峽兩岸的親屬、黃埔同學、臺灣“中國統一聯盟”的同仁、“中華合唱團”團員、政學界好友、建國中學的眾多師生,都以各種方式,懷念這位愛國、愛人、敬業、正直的黃埔軍人音樂家。
我于1998年6月退休后不久,被甘肅省黃埔軍校同學會聘為《甘肅黃埔》雜志的編輯,十多年來,遵循黃埔軍校同學會首任會長徐向前元帥“為黃埔同學立言,為祖國統一盡力”的宗旨,把它當成自己應履行的光榮使命,努力發揚愛國革命的黃埔精神,把為黃埔同學服務、為黃埔軍人立言的工作盡力作好,以告慰先輩的在天忠魂。
相關新聞
 請關注微信公眾號
請關注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