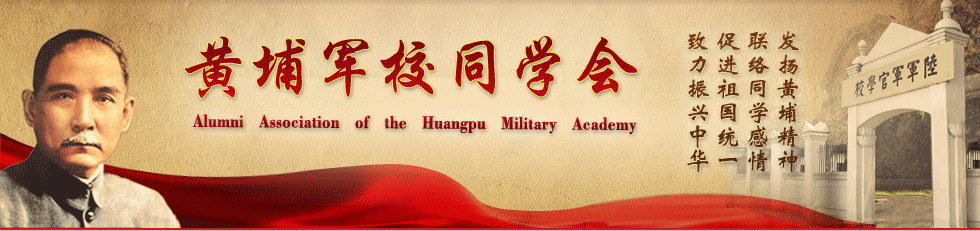
2017年3月4日,我們到浙江臺州市黃巖區訪問了抗戰老兵盧良鑒先生。盧老為我們講述了他的故事:
在小學與“省立六中”師范班學習
我1919年農歷九月十八日生于黃巖縣西部山區的烏巖鄉。父親盧秀金在我8歲時就不幸去世了,留下了兄弟4人,我是最小一個,母親含辛茹苦將我們拉扯成人。兒時,我在鄉里的烏巖小學讀書。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日軍步步緊逼,侵略我國,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在校時,教師經常向我們講抗日救國的道理。老師要大家記住,我們的敵人是日本侵略者,我們一定要團結起來,抗擊日本鬼子的侵略,保衛自己的家園。
小學畢業后,我考進了設在臨海(今椒江)的浙江省立第六中學(今臺州中學)師范部(當年學校分中學部、師范部兩部分)。上學時,母親再三叮嚀:“你的三個兄長都去當兵了,只有你一個兒子留在我身邊,別走了,讀好師范,將來在鄉里當個教書先生。”
父親去世得早,家里經濟困難,讀師范可免交學費,這也是母親讓我報考師范學校的初衷之一。師范部是四年學制,不過,到了畢業那年(1938年),學校已更名為“浙江省立臺州中學”了。
當時,日軍侵華的戰火燃及大片中國土地,和平寧靜的生活遭到破壞,尤其是淞滬戰役爆發后,日機瘋狂地向周邊地區狂轟濫炸,臺州也難于幸免。同年8月,5架日機轟炸黃巖城。日艦出現在椒江海面上,炮轟海門。日機對黃巖城區民房大肆轟炸,百姓紛紛外出逃難,離鄉背井,流離失所。師生耳聞目睹,個個義憤填膺。
學校的老師向我們講了許多抗日救國的道理,其中有一位老師叫項風(又名項道鵬)說道,日本鬼子打過來了,國之不存,民將焉附?每個愛國青年都要奮勇當先,保家衛國,抗擊日寇的野蠻侵略。
當時局勢緊張,大街小巷,各行各業的人都喊出了“抗日救國”的口號。戰火漸漸逼近臺州之時,學校組織了一個戰地服務團,為前線將士服務。項風老師成為戰地救國服務團的團長。在會上,他鼓勵大家踴躍報名,上前線殺敵報國。
那時兵荒馬亂,人心惶惶,老百姓紛紛四出逃難。我們問項老師:“今后該怎么辦?究竟怎樣才能報效國家呢?”
項老師說:“如果不愿做亡國奴,就應當到后方去,學會殺敵報國本領。我愿意帶領大家一起到后方去。”
投考黃埔軍校
同學們熱血沸騰,許多人決定跟項老師一起走,同行的還有女生。經過十幾天的跋山涉水,終于到了湖南。在長沙,時局依然動蕩不安,大家只好分頭尋找門路,各奔東西了。一位同學叫韓發逵,去了延安(解放后成為嘉興地委書記),還有一個女同學叫鄭曼(原名鄭香云),路橋人,投考了戰時干部4團(后成為詩人臧克家的夫人)。我與表兄盧巽良、許承志(臨海人,后來去了臺灣)以及其他5個青年,聽說陸軍軍官學校正在招生,于是大家去報了名。
錄取后,在教官帶領下,我們從長沙出發,步行20多天才到達湖南武岡縣陸軍軍官學校二分校所在地,校舍設在武岡縣蕭家祠堂。班里有個同學叫孔令晟,與我很熟悉,他是常州人,聽說是財政部長孔祥熙的兒子(后成為臺灣海軍陸戰隊中將司令)。
在軍校,我們既要學習排兵布陣、戰略戰術,又要訓練體能,學習生活十分緊張。由于日軍大舉進攻,大片國土淪陷,形勢越來越嚴峻,原來陸軍軍官學校為3年學習期限,改成一年半,沒有見習期(后來又回校補訓一年畢業)。在學校里,我們學會了抗擊日寇的基本本領后,就走上了炮火連天的戰場。
上前線抗擊日寇
1939年底,我被分派到第90軍61師戰車炮連任少尉排長。軍長李文,師長鐘松(浙江松陽人,黃埔2期學生),還有屠岳嵩等人也在同一個師團。剛剛報到,部隊就開拔了,我隨部隊直接上了前線,61師駐防在陜西省韓城縣楊村。1942年10月,我又調到82團(團長石滌非)的8連任排長。
我所在的90軍與日寇有過一次非常激烈的交戰。日軍在進攻我河南、山西防線失利后,派出裝備更加精良的板垣師團,準備搶渡黃河,打開我方前線缺口,然后,進攻大西南。一旦黃河防線失守,就會直接威脅西南地區的大片土地,陪都重慶亦會受到嚴重影響,后果不堪設想。
板垣師團的一支部隊企圖從禹門口(即龍門,大禹治水的地方)渡河,繼而進攻西安。可是守衛黃河前沿的預1師只有一個連的兵力布防在禹門口。師長擔心力量不足,向駐扎在附近的61師的石滌非團長請求支援。
此時,我已擔任61師的上尉連長,我們這個連隊是全師的前衛部隊,也是精銳力量。石團長下令,由我帶領全連弟兄迅速趕赴前線增援,必須在拂曉前抵達禹門口。于是,全連戰士整裝出發,星夜趕往戰地。黑夜行軍,不能亮燈,否則會暴露目標,被日機轟炸。經過近一夜的急行軍,終于在天亮前趕到了禹門口,駐守陣地預1師的那位連長見到增援部隊趕來興奮極了,全體官兵士氣大振。
我與連長寒暄了幾句后,馬上帶領幾個排長到前沿熟悉陣地。我軍布防的黃河沿岸,與敵軍只是隔岸相對,用望遠鏡觀察,可見到對岸敵人布防的陣地。只見他們正在登上從老百姓那里奪來的木船,也有橡皮艇,準備搶渡黃河,日機還不時在低空盤旋偵察,一場硬仗一觸即發。
我們伏在壕溝里等待上級的信號。開始時,日寇用大炮向我方陣地猛烈開火,我軍未予回擊。接著,又用小炮、機關槍向我方陣地大肆掃射。我知道,這是日軍慣用的伎倆,他們想借炮火試探我軍陣地虛實。
雙方軍隊隔著黃河,遙遙相對。當日軍木船與橡皮艇漸漸駛近黃河中線時,我軍開火的信號彈發射了。頓時,我軍槍炮齊射,掃向日軍船只。
在我軍猛烈火力下,敵船被打得暈頭轉向,在水中回旋,橡皮艇被打碎,不少船只被擊沉,日本兵紛紛掉進水里,不久,就被滔滔江水所吞沒。可是,日軍不甘心失敗,多次重整殘兵向我方撲來。我軍多次阻擊,越戰越勇,決不讓日寇越過黃河。
天亮后,日軍見我方炮火猛烈,久攻不下,以為我軍增援部隊到了,就停止進攻。其實,我方只有兩個連的兵力,大約200多人在禹門口駐守。我想,如果對方繼續硬攻,我軍有可能很難堅守下去。那次阻擊日軍強渡黃河戰斗的勝利,使得我軍士氣大振,我們也獲得了軍部通報嘉獎。
開辟滇緬公路、接收日軍物資
1943年初,鐘松師長調到第2軍當副軍長(時王凌云為軍長),軍部設在云南曲靖。鐘松師長把我也調到第2軍任上尉參謀。
由此,我離開了西北戰場,隨軍到了云南。
其時,日軍已經占領了我國東南沿海的大部分地區,以及主要的運輸干線,外部支援我國的物資很難從海路運到抗戰前線。由此,中美雙方正在搶修滇緬公路。第2軍授命與第1軍(遠征軍)匯合,準備一起打通滇緬公路。
正當我所在部隊趕到騰沖準備出境時,接到中印公路收復的捷報。滇緬公路通車后,大批國際援助物資源源不斷地通過這條公路送到西南各地。
幾個月后,我接到黃埔軍校成都本校來電,我們那一期(尚未完成學業)的人要回校補訓。由此,我被上級派到貴州普安縣補訓。只是幾年下來,南征北戰,風霜雨露,槍林彈雨,過于疲勞辛苦,加上補訓期間,強度過大,我得了肺病。
1944年初補訓結束后,經上級批準,我到貴陽大哥家養病一年。那時我家四個兄弟都在貴陽。大哥盧良船在防空學校當軍需官,二哥盧良舟是防空學校經理科中校科長,三哥盧良駿是防空學校照測總隊上尉軍醫。
我們兄弟四人誰也沒有想到,會在貴陽重逢,開心極了。
1945年上半年,鐘松再次被調到西北地區,擔任新編36軍軍長,駐地在陜西渭南,我也被派到36軍任職。同年7月,我正準備由貴陽出發到渭南時,接到鐘松軍長手諭,派我直接到河南洛陽的新編36軍28師師部報到,任少校參謀。當時28師的師長是王應尊,駐扎在河南新鄉。部隊正在休整,積蓄力量,準備反攻。
一天晚上,大家忽然被一陣陣的鞭炮聲驚醒,街道上熱鬧非凡,我們打開窗戶,只見大批市民歡天喜地跑到街上,高聲歡呼:日本人投降了!聽到這個喜訊,我們全都激動得流淚了,開心得不知說什么才好,終于盼來了久違的和平。
抗戰勝利后,我所在的部隊任務是接收洛陽,主要是接收日軍的輜重、馬匹、車輛、彈藥、糧食等,并做清點記錄工作。此時,日本人垂頭喪氣,早就失去了往日的威風。渴望已久的和平終于降臨了。
1946底,我返回老家黃巖的烏巖鄉,看望久別的母親與鄉親。鄉親們聽說前線戰士凱旋歸來,個個歡天喜地迎接我們。
那年我剛好28歲,巧遇到烏巖做客的陶芝韻。相識不久,我們就在烏巖結婚了。婚后,部隊又來了急電,催我馬上歸隊。軍令如山倒,百般無奈之下,只好帶著妻子一起回到部隊所在地西安。此時,我已成為軍部參謀處中校科長,妻子作為家屬隨軍。
內戰炮火接近西安的時候,我的大兒子已經出生,妻子抱著兒子由西安乘機到上海,然后,返回故鄉黃巖。
此時,我擔任第5兵團中校參謀,跟著部隊撤退到四川成都。原計劃要繼續撤退到西藏,只是解放軍向大西南進軍的速度比我們快得多,切斷了我們的退路。當時,解放軍向國民黨軍隊宣傳,只要棄暗投明,宣布起義,既往不咎。
1949年,我所在的部隊在成都宣布起義。
新中國成立以后
解放后,我被送到西南軍政大學學習。離開學習班后,我參加了成渝鐵路的建設。爾后,我們準備到朝鮮參加抗美援朝,正在大家整裝待發之時,朝鮮停戰了。
1953年,我轉業返回了故鄉。回到黃巖后,組織根據我的檔案,知道我是臺州中學師范部的畢業生,由此,縣教育局派我到直坑小學教書。
聽到這個消息,我興奮極了,心想,現在好了,幾個兄長都在外地打拼,我是小兒子,果真實現了母親多年來的愿望,在結束戰火紛飛的離亂生活之后,在家鄉當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教書先生,過上和平幸福的生活,在家侍奉老母頤養天年了。
1958年,我回到老家烏巖參加農業勞動。
到烏巖不久,正好趕上當地要興建水庫,烏巖村民被移民到雙浦,我們全家只好搬到雙浦去住。剛到雙浦時,我們借住在一個廟宇里,那個廟原來有乞丐住著,他們將乞丐趕走,我們這些移民住了進去。
在當農民的那些日子,我還年輕,當過兵,身強力壯,各種農活,一學就會,什么耕田、種地、挑擔、打柴,樣樣活計我都干過。雙浦生產隊的社員對我們全家不錯。我與其他社員一樣勞動,靠生產隊的分紅,以自己的勞力與雙手養活全家人。
在農村勞動20年后,到了1978年,我恢復了教職、公職,也恢復了教齡,重新成為一名教師。我在上輦中學教書,再次踏上久違的講臺。只是我已快滿60歲,到了退休年齡。
20世紀80年代后,黃巖縣的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我參與籌組黃埔軍校同學會工作,并當選為黃巖縣的政協委員。
自此以后,我與大家一起做黃埔軍校同學會的工作,幫助尋訪黃埔同學,在政協參政議政,出席政協的各種會議。
時至今日,市委、區委統戰部的領導與干部還經常來探望我,每到節假日,街道、社區、志愿者也會帶著慰問品來看望我們。
這些年來,我在家中將練習書法、作畫作為消遣。一直到今天,我仍每周到黃埔軍校同學會辦公室上班。他們擔心我年齡大,怕我在路上有個閃失,勸我在家中辦公。不過,我仍堅持每星期至少要到同學會去兩三次。
1994年,我帶著老伴到臺灣探親訪友,在臺灣住了兩個多月。我們尋訪了昔日的親朋故舊,見到了許多在抗戰中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戰友、老長官。
解放前后,我家四個兄弟各奔東西,一個去了臺灣,一個在河南,一個到了成都,只有我一個人回到黃巖。我的岳父在抗戰勝利后,去臺灣接收日資銀行。自此定居臺灣。那次到臺北,我也去探望了他們二老。
2015年,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活動中,中共黃巖區委組織了“尋訪老兵”活動,許多中小學生與志愿者到我家來慰問。
我還參加了邊防總隊臺州邊檢站和江口中學聯合舉辦的“聽老兵講抗戰故事”活動。在學校與軍營中,我向同學與戰士們講述了當年的抗戰往事、我一生的經歷、晚年的幸福生活,我想讓人們銘記戰爭的苦難與勝利的光榮。
2016年2月8日,剛好是我與老伴陶芝韻結婚70周年紀念,許多志愿者不知從哪里聽到這個消息,紛紛趕來為我們祝賀。
現在,我們夫妻的退休金加起來每個月有1萬元左右,生活無慮,兒女孝順,身體健康,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們深深地感激黨和國家以及黃巖各級領導干部、群眾與志愿者對我們黃埔老兵的關懷!
相關新聞
 請關注微信公眾號
請關注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