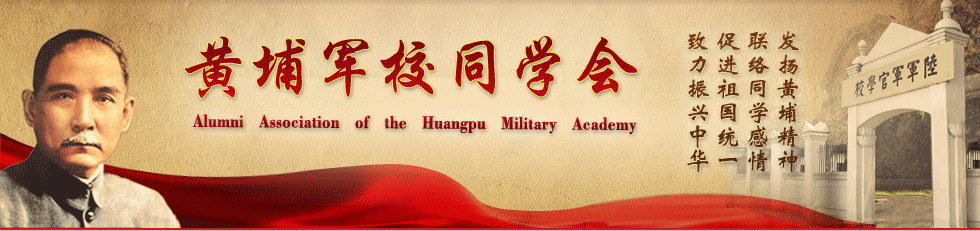

劉元發向后輩回憶當年慘烈
如果不是劉元發自己站出來,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隱居小山村60多年的老農民,竟然是曾立下赫赫戰功的遠征軍戰士。
現年91歲的劉元發是梅州興寧合水鎮羅英村人,讓他“說出自己的故事”的動力,源于今年9月初《羊城晚報》對遠征軍老兵楊劍達重回故鄉梅縣的報道,“我以前一直不敢說,也不愿意說。沒想到,現在社會這么認可遠征軍。”
劉元發說,現在老了,就想在有生之年再見一見戰友。說到這里,身體硬朗、吐字清晰的劉元發哭了:“生死與共的好戰友,你們在哪里,松山戰役過去快70年了,我還經常夢見你們。”
昨天,在他的農家小院里,劉元發講述了自己赴緬甸、過印度抗戰的傳奇經歷。
猛低頭,躲過日軍致命一槍
劉元發出生于1921年9月。他16歲那年,抗日戰爭爆發,興寧籍的副師長陳侃四處招兵買馬,1939年,陳侃當上第9集團軍第1挺進縱隊司令,他專門派人在興寧設點招收學生軍,劉元發參軍了。經過一年的訓練,劉元發被編入挺進縱隊任班長,他清楚記得,當時的支隊長叫賴梁東,是江西人。邊訓練邊打仗。有次在福建龍巖,與日本鬼子距離僅500米展開激烈戰斗,“‘嗖’,日本鬼子一槍打過來,我本能地一低頭,前額腦門上一陣麻辣,鮮血頃刻直流,敵人的子彈只擦破了頭皮,幸虧經過戰斗,熟悉日本槍打過的聲音,頭低得快,要不然早就腦袋開花命歸西天了。”
后來劉元發升為排長,后又調到云南昆明行營交通處運輸大隊,負責運送從越南河口到昆明的槍支彈藥,運送彈藥期間從未出過事,深得交通運輸處少將處長顏健華(廣東連平人)的賞識,并住在顏健華的家中,與年約50歲的顏健華情同父子。
一年后,在顏健華的推薦下,劉元發帶薪帶職,到國民黨中央軍校第五分校駐騰沖干訓班炮兵科學習。學習結束,劉元發被委任為少尉排長,自主選擇到興寧老鄉鐘彬任軍長的71軍,被安排到輜重團。劉元發至今仍記得,當時輜重團團長是吳濤,副團長是何中天。
攻龍陵,日軍炮彈炸傷大腿
1944年,劉元發所屬部隊接到命令,從寶山出發攻打松山。松山山勢險峻,以滿山是高大的松樹而聞名,山下是橫穿而過的怒江。戰斗打得非常慘烈,日本人在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山上挖了很多山洞,筑成堅固的防守陣地,洞里儲藏有很多糧食和彈藥。每當我軍沖鋒時,敵人就居高臨下,在洞門口利用機槍掃射和炮擊我軍。劉元發說,28師師長劉又軍也是興寧人,經過松山戰役,28師只剩下50多人。剛開始,日本鬼子還不時在夜間偷襲我們。后來,我方用大炮猛烈轟擊,18架飛機輪番轟炸,炸得松山草木不存,掀開的全是厚厚的泥土,把日本兵炸得抬不起頭來。最后,日軍只剩下30多人,被我軍層層包圍之后出來投降。“日軍被俘后,我還和日本俘虜扳手勁比試日本鬼子的力氣,最后還是我贏了。”劉元發侃侃道來,十分自豪。
松山戰役結束后,劉元發隨軍攻打緬甸交界的龍陵、回龍山等,“在攻打龍陵時,我被敵人的炮彈炸傷左大腿,這次也非常的幸運,差一點就炸斷了大動脈,至今左腿留下深深的傷疤。”由于當時后方醫院還在昆明,劉元發在戰地醫院簡單治療后,一直隨部隊追打日軍到緬甸。之后部隊休整了一段時間,然后坐飛機到達印度新德里整訓,三個月后接到命令回國,先坐飛機到貴州,然后坐汽車到廣西,繼續整訓準備攻打駐守桂林的日軍。就在部署攻打任務的第二天,日軍投降。
想戰友,做夢都盼能見一見
抗日戰爭勝利后,劉元發到上海市民政局工作,兩年后,他覺得自己適合經商,辭職后輾轉東北一帶做藥材生意,賺了一些錢。1949年11月,思念家鄉的劉元發單身途經江西回家,路上遇到一群土匪,身上的錢財被洗劫一空,連身上穿著的棉襖也被搶走了。一路徒步,劉元發終于回到老家,娶妻生子,孩子們都很爭氣,在村里蓋了一棟樓房。后來,妻子、兒媳、兒子先后病逝,孫子們都出去打工了,留下劉元發一個人待在院子里。
今年已經91歲了,劉元發每天仍然樂呵呵的,自己種菜、做飯,唯一的遺憾是,他所有的證件包括國民黨頒發的抗戰獎章,在30年前一場大火中丟失了。
村干部劉新添告訴記者,劉元發做人很低調,1949年回到村里后一直沒告訴大家他參軍打仗的“威水史”,大家都知道他是國民黨老兵,“他在我們村里隱居了60多年”。村里曾想為劉元發申請補助金,但因缺少證件證明,戰友要么死去了,要么失去了聯系。“我們都相信他是真的,但現在沒證明,民政局也無能為力。”
記者與國內幾個關注遠征軍老戰友的團體聯系,劉元發講述的部隊番號、首長姓名等都絲毫不差,但遠征軍名冊早已丟失,無法查找劉元發到底在哪個師部。記者聯系過七位71軍的老兵,但電話要么打不通,要么接電話的人說“老兵已去世”。
羊城晚報記者 尹安學
 請關注微信公眾號
請關注微信公眾號